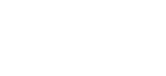在全球贸易摩擦常态化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关税政策突变已成为跨境交易中不可忽视的“黑天鹅事件”,这一事件又会进一步导致整个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违约风险。当合同未明确关税风险分担条款时,究竟合同的哪一方应该承担关税上涨导致的成本激增的风险?面对税率飙涨至125%的极端情况,企业能否以“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突破合同刚性约束?传统司法裁判中“关税属于商业风险”的固有逻辑,是否因本轮超幅度加税而松动?本文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为背景,针对中美“关税战”引起的常见合同履约风险问题,结合最新关税政策与典型司法判例,深度解析跨境供应链环节中关税与制裁风险的分配规则,揭示新贸易战形势下合同条款设计的关键路径,为企业构建“法律盾牌”提供实操方案。
一、跨境贸易或其他合同中未约定关税风险分担条款时,哪一方需承担关税上涨导致的额外成本?[1]
若跨境贸易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关税风险分担条款,在无其他法定事由(如情势变更、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关税上涨导致的额外成本通常应当由合同原先约定或国际惯例、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关税义务的一方承担,例如,在中国企业经常在国际贸易合同中采用的FOB价格术语下,关税上涨产生的额外税费通常由货物进口方承担,如果采用DDP(Delivered Duty Paid,完税后交货)价格术语,则由货物出口方承担。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或其他类型的合同,在无特别约定和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即便遭遇关税上涨,当事人仍应当根据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价格继续履行合同,不能仅凭单方意愿要求修改合同交易对价。若一方在合同未约定调价机制且无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因关税上涨直接要求变更价格而拒绝履约,可能被认定为违约行为,这也是企业在面临关税调整后履行合同的常见商业风险之一。
二、关税上涨导致进口成本和生产成本激增,需承担关税成本的一方能否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履行合同?[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3]和第五百九十条[4]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法律规定的定义和以往司法实践中的普遍观点,当相关进出口合同及其他合同约定适用中国法时,我们认为关税上涨通常难以构成中国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具体理由如下: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常见的有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异常事件及政府禁令等,其核心在于相关事件无法预见,并将会导致合同实质上无法履行。但是中美关税政策调整存在于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背景下,通常不构成不能预见,而且关税上涨并不会直接导致相关合同无法履行,关税上涨仅仅增加了进出口双方的交易成本,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会导致承担关税成本的一方经济利益受损,但并不会导致合同实质上无法履行。因此,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一方援引“不可抗力”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会被认定为己方违约并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税上涨导致进口成本和生产成本激增,需承担关税成本的一方能否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合同?[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6]规定,情势变更事件应当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并且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因此,当相关合同中并未约定关税调整条款并且适用中国法时,在关税上涨时如果任何一方希望援引情势变更原则主张变更合同,则应当证明:关税上涨的不可预见性以及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此外,应予注意的是,与不可抗力不同的是,情势变更需要由当事人请求裁判机构进行确定,在合同双方不能及时协商解决争议时,如果当事人希望援引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变更合同,则需要及时向裁判机构明确提出相应主张,并由裁判机构进行认定。
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一任期期间,已经拉开了中美“关税战”的序幕,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在该期间当事人因中美关税上涨,主张该情形构成情势变更而请求裁判机构变更合同的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倾向于认为:两国之间加征关税属于国际贸易中较为普遍的商业风险、作为从事进口业务的商事主体应当对于加征关税具有预见能力,在此基础上仍约定由一方承担税费,则该方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未能证明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基于前述理由,裁判机构大多不会支持当事人一方变更合同的请求(详见(2023)内02民终1704号案、(2021)粤1971民初12896号案、(2019)川0193民初10989号等)。
但是,截止本文写作之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将针对中国的关税上涨至125%,涨幅达到105%,我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宣布将针对美国的关税上涨至84%,而上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关税上涨幅度最多时仅为25%。考虑到本次中美双方的关税上涨幅度均已经远高于上一次,并且税率也创历史新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两国之间加征关税的范畴,并且不论是84%还是125%的税率都将对于承担进口税的一方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若当事人因本次关税上涨以情势变更为由向裁判机构请求变更合同,裁判机构未必会机械地沿用此前的观点,若当事人能够证明本次关税上涨并非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情形,裁判机构有一定概率支持当事人变更合同。
四、其他制裁措施能否视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合同相关方能否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或要求变更合同?[7]
与中美“关税战”并行的还有贸易战下的各种制裁措施。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成为近期热点问题之前,另一高频热点问题便是“制裁”,例如家喻户晓的美国对华进行芯片制裁、美国对俄进行全面制裁等。美国的对外制裁主要通过将被制裁主体列入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以及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管理的各类制裁清单来实现,BIS主要负责与出口管制相关的制裁清单的管理,包括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未经核实清单、被拒绝人员清单;OFAC主要负责与金融及资金相关的制裁清单的管理,包括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清单(SDN)、非SDN军事综合体企业清单。
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各类制裁清单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应当判断的是某主体被列入制裁清单是否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之情形。美国的各类制裁清单均存在公开的法律或政令作为依据,而我国法院通常认为法律或政令属于当事人应当了解并知悉的内容,当事人对于自身存在可能被列入制裁清单的行为应当提前预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制裁仍然有可能满足“不能预见”之前提条件,如俄乌战争的突然爆发导致的制裁,便不宜认定为可以预见的情形。至于某项制裁措施是否属于“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则应在个案当中结合该项制裁措施是否导致被制裁主体不能通过替代方式履行合同,被制裁主体是否有途径进行司法救济等因素综合判断。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外国主体被列入制裁清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仅在特定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俄乌战争爆发导致俄罗斯企业被制裁而无法履行合同),进而认定合同无需继续履行或应当变更合同内容。
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对于各类制裁清单是否属于情势变更,应当判断的是某主体被列入制裁清单是否导致商业合同的履行内容发生“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最常见的判断依据便是商品价格是否存在严重的波动。结合我国法院在各种类型的司法判例中对于情势变更的认定标准,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制裁措施导致履约成本的浮动不大,那么法院不会认定制裁措施构成情势变更,仅在制裁措施导致一方的履约成本成倍上浮且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法院才有可能认定制裁措施构成情势变更,进而对合同内容进行调整。
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适用情形下如何处理关税政策变化?
对于中国企业涉及的国际贸易合同,交易双方往往分属于不同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缔约国,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那么CISG将优先适用于该国际贸易合同。因此,在CISG背景下了解关税政策变化导致的履约风险也非常必要。
CISG第79条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基于此,主张因“障碍”免责需满足以下条件:(1)不可控制性,即障碍超出当事人控制范围;(2)不可预见性,即障碍在订立合同时无法合理预见;(3)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性,即无法通过合理措施避免或克服障碍影响;(4)直接因果关系,即障碍直接导致履约失败。上述要点(1)至(4)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不可抗力的原则本质相同。因此CISG中的“障碍”的构成要件本质上与我国不可抗力免责的构成要件基本一致,对于关税变化的处理应当同问题二:即关税变化并未导致合同履行的障碍不可避免或克服,故难以适用CISG第79条予以免责。
CISG本身对情势变更没有明确条款约定,而对于CISG下的“障碍”是否包括了艰难情形(Hardship,即中国法下的情势变更),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国家法院处理适用CISG的案件时,曾经将货物价格上涨了70%认定为订立合同时不能被合理预见到的且显著加重履约成本致使合同陷入显著不公状态的环境变化,构成CISG下的“障碍”[8]。虽然CISG对于情势变更的适用不明,但合同双方在约定适用或根据国际私法冲突规范适用中国法时,中国法下的情势变更有关规定也可以填补CISG空白并予以适用。
六、企业如何通过在合同中设置相关条款以减少关税变化导致的履约风险?
第一,企业可通过在合同中设置价格调整条款来应对关税变化风险。此类条款的核心作用是允许双方根据关税变动动态调整合同价格,避免单方因关税变化而承担过高成本。具体设计时,需明确关税调整的触发条件,例如规定税率变动幅度超过合同总价的5%或政府公告作为依据,并约定价格计算公式(如新价格=原价×(1+关税增幅比例))。例如,合同可约定:“若进口关税税率上调且增幅超过5%,双方应共同分摊买方因此额外增加的成本,买方应在30日内提供政府官方公告或缴纳进口税的证明作为调整依据。”
第二,为应对关税变化导致合同基础条件失衡的风险,无论双方是否就调价计算方式达成一致,企业都可入重新谈判条款。这类条款赋予双方在关税变动对合同经济性产生重大影响时(如成本增加超过合同总价的20%)重新协商的权利。设计时应限定重新谈判的期限(如15日内启动),并明确未达成一致时的处理方式,例如终止合同。示范条款可为:“若任一方因关税调整导致履约成本增加超过20%,双方应在15个工作日内启动协商;若60日内未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可终止合同。”
第三,合同中还可以明确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条款的适用。双方可将关税重大调整列入不可抗力事件清单;或约定关税剧变导致显失公平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例如上述第二条的“示范条款”。
第四,争议解决和法律适用条款的设计同样关键。我们理解涉及关税和制裁风险的合同通常涉及中国境内外当事人,我们建议企业应优先在合同或订单中将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并尽可能选在中国境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仲裁庭更能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公平合理地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仲裁裁决也能方便地在境内外得到承认与执行。另外,中国企业也应尽可能选择适用更为熟悉的中国法律为合同的准据法。
注释:
[1] 参考案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2876号判决书;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91民初1693号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02民终1704号判决书。
[2] 参考案例: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10989号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兵民终54号判决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2021)兵01民初5号判决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5] 参考案例: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02民终170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1)粤1971民初12896号民事判决书(采购方主张情势变更);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10989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申5023号裁定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7]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958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8009号判决书。
[8] Scafom International BV v. Lorraine Tubes S.A.S., Hof van Cassatie van België/Cour de cassation de Belgique (Belgian Supreme Court), Belgium, 19 June 2009 – C.07.0289.N, CISG-online 1963.